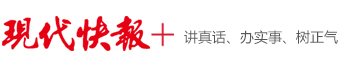精神異常,始終是流行文化中最迷人也最持久的“母題”之一。
流行樂迷,津津樂道于Talking Heads樂隊的《Psycho Killer》,從20世紀70年代西裝革履的神經質搖滾,直到今天余音猶在;
資深影迷,鐘情希區柯克的《驚魂記》,詭異的題材、意外的故事情節、低預算的黑白制作,竟開了電影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的先河;
還有暢銷小說讀者,愛倫·坡筆下《泄密的心》里那無法擺脫的心跳,將妄想與偏執的自我審判,變成了可供眾人傳閱的公共文本。
我們消費這些故事,在安全的距離外顫栗,將瘋狂他者化,仿佛它只存在于歌詞、銀幕與小說里。
然而,現實中的精神病學,其故事遠比任何虛構作品都更為曲折、荒誕與深刻。最近,譯林出版社推出的《從弗洛伊德到百憂解:精神病學的歷史》,正是由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前主席杰弗里·A. 利伯曼執筆,對這段歷程進行一次毫不避諱的祛魅與還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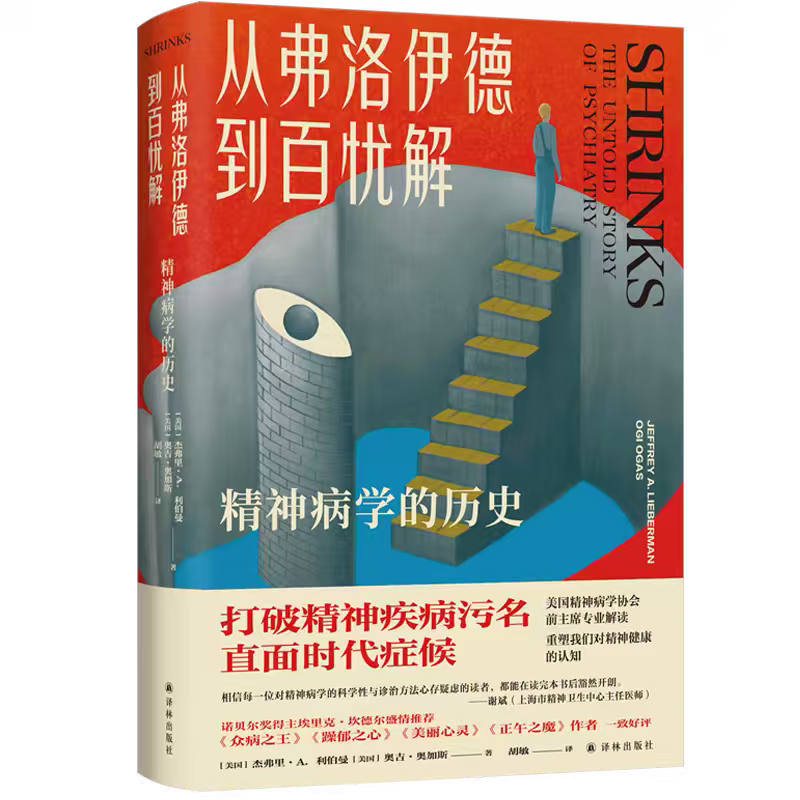
精神病學的童年,寫滿了試圖“拯救”卻近乎“謀殺”的荒誕筆記。
在科學的曙光降臨之前,絕望催生了各種匪夷所思的療法。美國醫生本杰明·拉什讓病人坐在旋轉椅上直至昏厥,試圖用眩暈“甩掉”精神疾病;葡萄牙醫生埃加斯·莫尼茲開創了腦白質切除術,用器械在病人顱骨鉆孔,駭人聽聞的手術,竟為他贏得了1949年的諾貝爾獎。
更令人心驚的是威廉·賴希的“生命能”學說,他讓患者擠進一個電話亭大小的箱子,脖子上掛著橡膠軟管,宣稱能匯集宇宙能量治愈瘋狂。這些如今看來近乎騙術的方法,當年卻獲得了主流醫學期刊的認可。
“善意與傷害的邊界,在那個探索的年代模糊得可怕。”
轉折發生在1952年。
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長期主導的精神病學,終于迎來了它的“科學元年”。《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的誕生,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將“沒有數據支持的弗洛伊德式假說”掃地出門。它創立了“主觀痛苦+功能損害”的診斷原則,將無數特立獨行的靈魂從“瘋子”的標簽中解放出來。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給精神分析學派帶來致命一擊的,正是其門徒亞倫·貝克。他創立的認知行為療法,成為首款經盲法試驗驗證的“循證心理療法”,一舉改寫了“談話療法”不科學的刻板印象。與此同時,藥理學迎來突破,氯丙嗪、鋰鹽相繼問世,科學家們終于找到了能真正作用于大腦的化學鑰匙。
埃里克·坎德爾通過研究海蛞蝓揭示了記憶形成的奧秘,榮獲諾獎。他的研究標志著,精神病學正在從談論“心靈”的玄學,轉向研究“大腦”的科學。
然而,當診斷標準日益明晰,治療手段愈發有效,精神病學卻面臨著一個比科學更復雜的敵人——社會的污名。
書中記錄了一個堪比《閣樓上的瘋女人》的現實案例:21世紀的紐約,一位罹患精神分裂癥的富家太太,被家人囚禁在別墅廂房長達四十年。當醫生發現她并建議治療時,家人的回答冷靜而殘酷:“體面比健康更重要。”
更反諷的場景發生在一場精神疾病籌款午宴上。作者觀察到,那些慷慨陳詞、呼吁破除偏見的來賓,幾天后卻紛紛私下聯系他,為家人求助,且無一例外地要求:“請不要告訴午宴主人。”
“我們終于能夠治療疾病,卻還沒學會如何面對病人。”
當全球每八人中就有一人受精神疾病困擾,我們逐漸意識到,這并非一組冰冷的統計數據,而是人類境況的一部分。從弗洛伊德試圖解讀夢的密碼,到百憂解精準調節大腦的化學平衡,精神病學的百年跋涉,本質上是一場人類對自身心靈發起的、最艱巨也最勇敢的探索。
或許,這本書最大的價值,不在于它羅列了如何區分“正常”與“異常”的準則,而在于它邀請我們進行一場思想的轉變:精神疾病不是一種身份的烙印,而是生命在某個階段可能經歷的一種狀態。
流行文化將瘋狂譜成供人消費的傳奇,而精神病學的歷史則告訴我們,理解與接納,才是超越恐懼的真正開始。

【書摘】
我很幸運,我親歷了我所從事的醫學專業歷史上最急劇、最積極的巨變,我見證了它從精神分析派的異教逐步轉變為基于大腦的我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精神病學系主任不久后,有人請我給 66歲的金太太會診。她因嚴重的皮膚感染入院,看起來長期未接受治療。這令人費解,因為金太太受過良好的教育,家境富裕。她畢業于醫學院,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亞洲實業家,按理說她可以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
我與金太太交談后,很快明白了為什么醫院請一名精神科醫生去看皮膚感染的病人。我試著問她感覺如何,她卻開始胡亂大喊,還做出奇怪、憤怒的姿勢。我不說話,默默地觀察她,發現她在和自己說話——或者更準確地說,她在和不存在的人對話。我無法與她溝通,于是我要求和金太太的家人聊一聊。第二天,她的丈夫和一雙成年兒女不情不愿地來到了我的辦公室。我反復勸說之后,他們透露,大約40年前,金太太從醫學院畢業不久后就出現了精神分裂癥的癥狀。
她的病讓家人蒙羞。盡管家境富裕,資源豐富,但金太太的父母和丈夫從未替她尋求任何治療。相反,他們決定竭盡所能防止外人發現她患有精神分裂癥。他們在寬敞的家中隔了一間廂房出來,有客人登門時就把她關起來。她很少離家,從不長時間外出,直到后來患上了皮疹。家人試遍了各種非處方藥,希望能解決這一問題,但皮疹蔓延并引發感染后,他們害怕了,給家庭醫生打了電話。當看到金太太的身上布滿膿腫時,家庭醫生懇求她的家人送她去醫院,診斷結果是嚴重葡萄球菌感染。
我目瞪口呆,復述了一遍剛才聽到的事實——過去30多年里,他們沆瀣一氣,讓金太太遠離外界,避免家丑外揚。他們毫不羞愧地一致點了點頭。我難以置信——這簡直是夏洛蒂·勃朗特小說里的情節,不該發生在21世紀的紐約。我直截了當地指出,他們拒絕給她治療的決定殘忍且不道德——雖說,不幸的是,這種行為并不違法,我敦促他們讓我們將她轉到醫院的精神科接受治療。他們滿腹狐疑地討論了一番,隨后拒絕了。
他們告訴我,即使金太太能夠被治愈,由此產生的后果對他們的生活和社區地位也太具破壞性。他們得向朋友和熟人解釋,時隔多年,金太太為何突然在公共場合再度露面,而至于金太太在這種情況下會有什么樣的言行,誰知道呢?金家認為精神疾病的污名太過可怕,寧愿任由這位曾經聰明伶俐、身體健康的女性繼續精神失常,沒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大腦不可逆地惡化,也不愿面對承認她患有精神疾病的社會后果。
幾代人前,精神疾病治療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診斷標準不可靠,精神疾病理論僵化。如今,最大的障礙不是科學知識的鴻溝或醫學能力的不足,而是精神疾病的社會污名。不幸的是,歷史上精神病學歷經了種種失敗,被視為不受歡迎的醫學繼子,如今這個污名已站不住腳,但還是留存了下來。
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對不同的種族、宗教和性取向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寬容,但作為一種每四人中就有一人面臨的非自愿的醫學狀況,精神疾病仍然被視為恥辱的標志,患者仿佛被戴上了紅字“瘋子”“神經病”“腦子有毛病”。想象一下,如果你受邀參加朋友的婚禮,卻突然抱恙。你更愿意說你是因為腎結石……還是因為躁狂發作,所以去不了?你是寧愿道歉,然后以腰部扭傷為借口……還是說你恐慌發作了?你是更愿意說自己得了偏頭痛……還是說自己因酒醉而難受?
我幾乎天天都會遇到這種羞恥和敏感的例證。來我們精神科看診的許多患者寧愿自掏腰包,也不愿走醫療保險,因為他們擔心被別人知道。還有一些患者不去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精神科門診看病,也不愿去紐約州精神病學研究所找我看診,而寧愿去沒有任何醫學專業標識的私人診所。很多患者經常從南美、中東或亞洲飛到紐約找我們看病,為的就是確保本國沒有人會發現他們在看精神科醫生。
幾年前,我在曼哈頓市中心的一場午宴上發表了一次關于精神疾病的演講,為精神病學研究籌集資金。隨后,我四處走動了一下,同參加活動的人寒暄。這些聰明、成功、外向的人都是薩拉·福斯特請來的,她是一位社交名流,她兒子患有精神分裂癥,在高三那年自殺。他們品著清燉三文魚,啜著夏布利干白,公開贊揚薩拉為提高公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所付出的無私努力,盡管他們之中沒有人承認自己有跟精神疾病打交道的直接經驗。事實上,他們對精神疾病的看法就像看待蘇丹的種族滅絕或印尼的海嘯一樣: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公眾關注,但與贊助人自己的生活相去甚遠。
幾天后,我在辦公室接到一位參加者的電話,她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編輯,問我能否幫幫她。她好像對工作提不起興趣,難以入眠,經常變得非常情緒化,甚至還會哭泣,她問我她是不是在經歷中年危機。我同意見她,最后我診斷出她患有抑郁癥。但在約定與我見面之前,她堅持要我完全保密,并補充道:“請你別跟薩拉說這件事!”
次日,我接到另一位參加者的電話。這位女士在一家私募股權公司工作,她20多歲的兒子從研究生院輟學,出來創業,她很擔心。盡管她贊賞兒子的創業精神,但這款旨在消除世界貧困的新軟件是他在一段行為古怪、失眠的時期構思出來的。經過評估,我的初步懷疑得到了證實:她兒子正處于躁狂發作的初期階段。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我接到了更多薩拉邀請的參加者的電話,他們為有成癮問題的配偶、有焦慮癥的兄弟姐妹、患有癡呆癥的父母、有注意力問題的小孩和仍然住在家里的成年子女向我尋求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薩拉午宴的客人中有半數聯系了我,其中還包括作為活動舉辦地的餐廳的老板。
這些人都受過教育,見多識廣,能夠負擔得起錢、能買到的最好的健康護理服務。要是呼吸困難或長時間發熱,他們可能會向私人醫生尋求幫助,或者至少會找最好的轉診醫生。然而,精神疾病的污名讓他們一直竭力避免尋求醫療幫助,直到后來在社交場合碰巧遇到一位精神科醫生。令人吃驚的是,他們都是應朋友之邀來參加那場籌款活動的,這位朋友致力于提高公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但他們之中誰都不希望薩拉知道自己的問題。
現在,終結污名的時機終于到來了。而且,我們現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們可以做到。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王子揚
(出版社供圖)